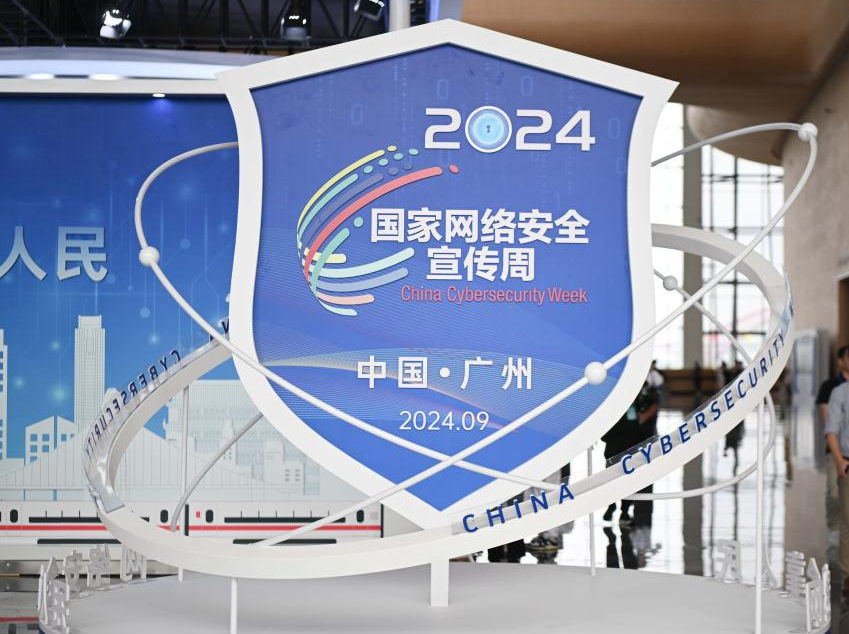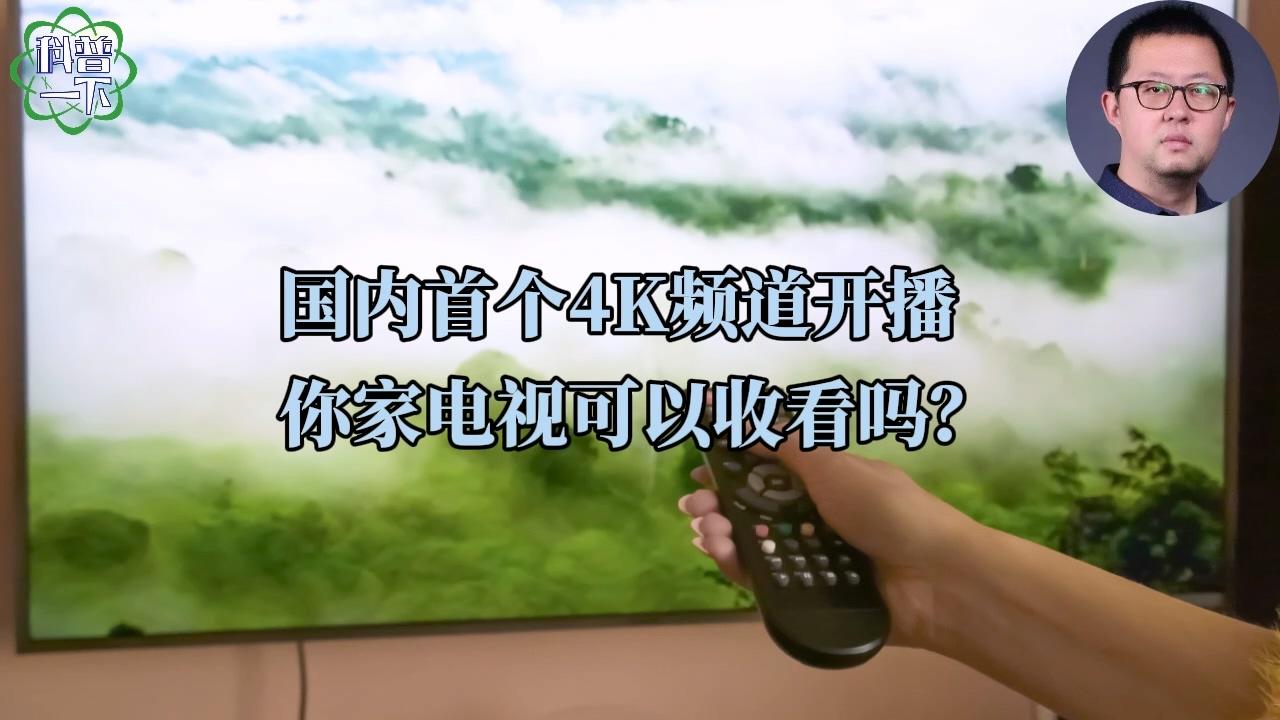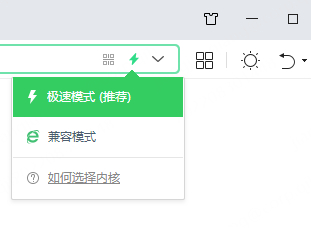科技日報記者 陳汝健
金銀絲線,繞指柔結,千年絕技翻飛于匠人指尖;金銀胎體上鏨刻出精美花紋,嵌玉綴翠。絲絲相扣間,盡顯繁復細膩,而又極盡華美。
花絲鑲嵌,又稱細金工藝,它融合花絲、鏨刻、銀藍和鑲嵌等工藝于一體,與景泰藍等同屬“燕京八絕”,其歷史可追溯至春秋時期。
在河北省大廠回族自治縣,花絲鑲嵌成為這里首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。“近年來,我們致力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,推動這項宮廷絕技‘飛入’百姓家。”4月8日,該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黨組成員、副局長田娟告訴科技日報記者。
以鏨為筆,三代匠人的接續傳承
“叮當——叮當——”
上午八點半,鏨刻聲在河北大廠良盛達非遺工坊內此起彼伏。80后馬維盛俯身于工作臺前,細細的金絲在他的鑷尖游走,如同春蠶吐絲般盤繞出寶相花紋。在他身后的展柜中,一個曾亮相冬奧會的和田玉冰壺正泛著溫潤光澤——壺蓋上纏繞的花絲,恰似一條時光紐帶,將千年宮廷絕技與當代審美悄然連結。
“鏨子就是我們的筆鋒。”作為馬家第三代傳承人,馬維盛時刻牢記父親馬福良的諄諄教誨。他的父親馬福良——這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花絲鑲嵌制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,至今仍保留著手工開鏨的傳統。
鏨刻技藝,實為小錘敲打各種鏨子,通過擠壓、抬鼓、剔刻等方式創造出平面或立體的裝飾圖案,鑲以珠寶。花絲技藝先將金銀抽成直徑0.1毫米至0.4毫米的細絲,再用堆、壘、編、織等技法使其躍然于工藝品之上。“長輩常說‘三分手藝七分家伙’,現在要加半句‘三分創新七分堅守’。”馬維盛談及父親跟著爺爺學徒時的經歷感慨道。
懸掛于展廳西墻上的祖傳鏨子陣列,無聲訴說著馬家三代人的傳承圖譜,默默見證著三代匠人的光陰故事——爺爺馬作文18歲在京城銀樓學藝時,學的正是清代造辦處的花絲鑲嵌技藝;父親馬福良為冬奧會制作冰壺時,將冬奧元素與中國傳統吉祥文化融為一體。
“每代人都在做同一道題,不過工具包在不斷升級。”馬維盛撫摸著父親制作的鏨刻工具,上百根鏨子按紋樣分類插在木盒中,像一隊整裝待發的士兵。
技術向“新”,宮廷絕技的破圈之路
“非遺不是躺在展館里當古董。”馬維盛的工作臺像座微縮的工藝實驗室,不僅堆放著傳統花絲擺件,還散落著新研發的“蝶戀花”系列胸針——這是他為傳承花絲鑲嵌技藝進行的“破圈”試驗。在他的推動下,花絲鑲嵌開始與3D打印技術“握手”:先用數字化建模確定結構,再用手工細金工藝點睛。
“戴上這些花絲胸針,就像一個行走的‘非遺體驗館’。”在馬維盛看來,傳承非遺的最佳路徑就是融入百姓生活。為此,他和工人用花絲鑲嵌技藝制作出胸針、耳墜和吊墜等首飾品,以及茶具、酒具等生活用品。
展廳內,除欣賞到花絲鑲嵌宮廷藝術精品外,還能品鑒、體驗非遺技藝。近年來,在馬家三代人的薪火傳承中,這項千年宮廷技藝在時空的更迭中不斷創新。如今,這里的花絲鑲嵌工藝產品類型多達千余種。
直播鏡頭前,定價數百元的花絲首飾,以及千余元的花絲茶具、酒具系列正成為新晉網紅。“更深遠的變化在于傳承鏈。”談及傳承與創新時,馬維盛告訴記者:“我創立了省級技能大師工作室,從最初的4人發展到如今的20多人,其中5人被評為省級工藝美術大師。”
千載金絲承古韻,萬錘銀鏨叩新聲。這項曾專屬宮廷的絕技,在大廠金火交織的花絲鑲嵌工坊里,正通過年輕匠人的巧思煥發新生。正如田娟在采訪中所說:“這些叮當作響的小錘,敲打的不只是金銀,更是傳統文化對接未來的接口。”